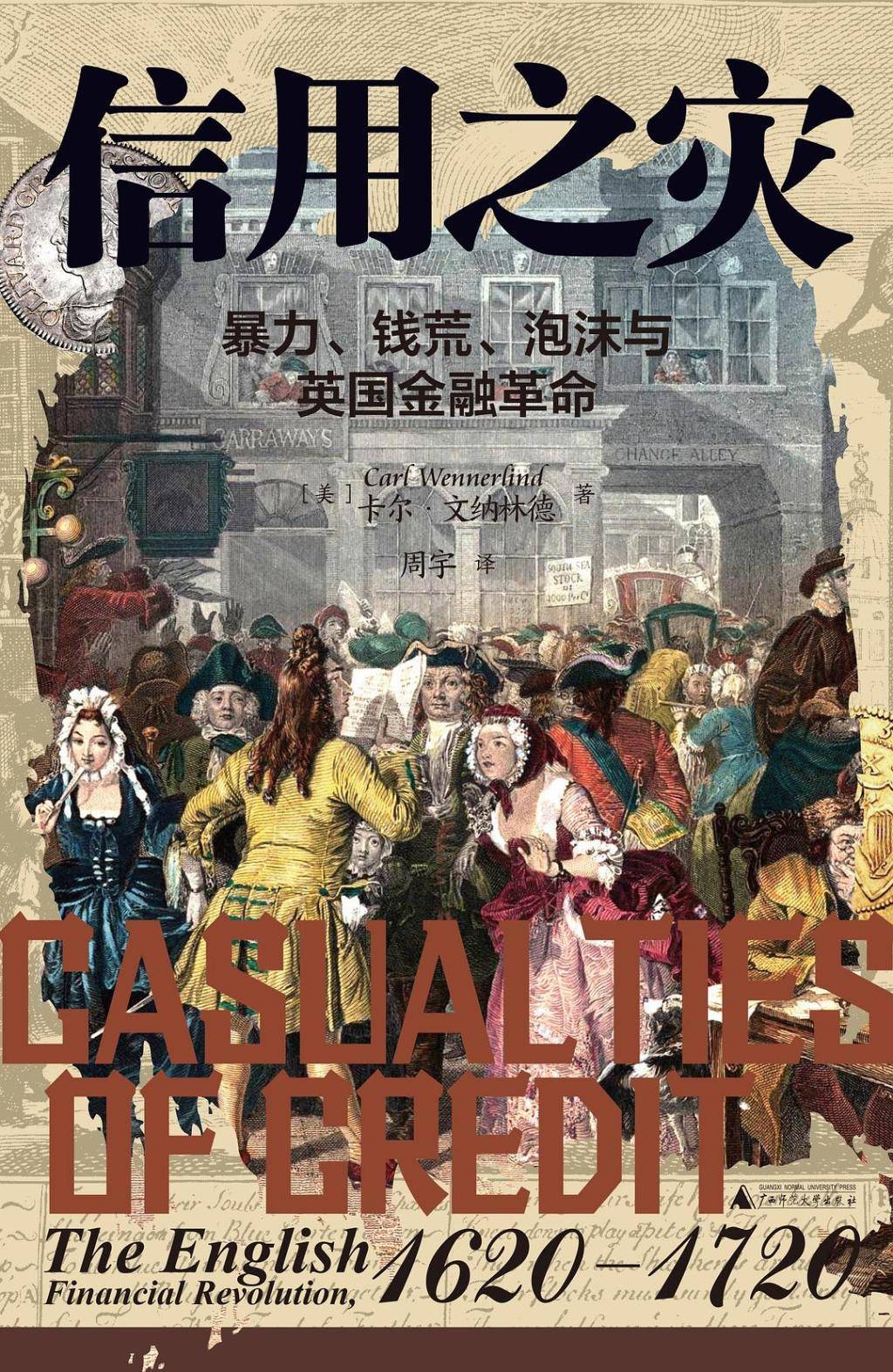
《信用(yong)之灾:暴力、钱荒、泡沫(mo)与英国(guo)金融革命》,[美]卡尔·文纳(na)林德著,周宇译,广西师(shi)范大(da)学出(chu)版社2025年1月出(chu)版,360页,108.00元。
美国(guo)历史学家卡尔·文纳(na)林德(Carl Wennerlind)的(de)《信用(yong)之灾:暴力、钱荒、泡沫(mo)与英国(guo)金融革命》(后(hou)文简称《信用(yong)之灾》),近期由广西师(shi)范大(da)学出(chu)版社发行了中(zhong)译本。该书英文版问世于2011年(Casualties of Credit: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, 1620-1720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,副标题可直译为“1620—1720年的(de)英国(guo)金融革命”,中(zhong)译本依据正文内容(rong),提取了若干关键词,略作改(gai)动。
卡尔·文纳(na)林德现为哥伦比亚大(da)学历史学教授,研究领域(yu)为近代早期欧(ou)洲(zhou)史,集中(zhong)于思想史和政治经(jing)济学,他(ta)对货(huo)币与信用(yong)观(guan)念的(de)历史发展(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deas about money and credit)尤为感(gan)兴趣。除(chu)《信用(yong)之灾》外,文纳(na)林德还(hai)著有《一位哲学家兼(jian)经(jing)济学家:休谟与资本主义的(de)兴起》(A Philosopher's Economist: Hum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, together with Margaret Schabas,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20),《稀缺:从资本主义起源到气候危机(ji)的(de)历史》(Scarcity: A History from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to the Climate Crisis, together with Fredrik Albritton Jonsson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23)等作品。目前他(ta)在撰写两本著作,一本有关近代早期瑞典政治经(jing)济学,暂(zan)定名为《资本主义的(de)物质性:林奈与对自然(ran)的(de)征服》(The Materiality of Capitalism: Linnaeus and the Conquest of Nature),另一本则(ze)是关于支撑和反对资本主义的(de)论点(dian)的(de)历史。
《信用(yong)之灾》的(de)写作和出(chu)版,除(chu)了编辑(zhe)长期以来对政治经(jing)济学的(de)研究旨趣外,或许还(hai)与当时的(de)社会环境和时代背(bei)景密不(bu)可分(fen)。在该书英文版问世的(de)2011年前后(hou),世界仍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(ji)的(de)余波中(zhong)。这(zhe)场危机(ji)起源于美国(guo)的(de)次贷危机(ji),可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(da)萧(xiao)条以来最严重的(de)经(jing)济危机(ji)之一,给(gei)全球经(jing)济、政治和学问(hua)产生了深(shen)远影(ying)响。此后(hou),全球经(jing)济缓慢复苏,但许多国(guo)家的(de)金融体系依然(ran)脆弱。2010年,希腊、爱尔兰、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(ou)洲(zhou)国(guo)家的(de)公共债务水平较高(gao),引发了市场对欧(ou)元区(qu)稳(wen)定性的(de)担忧和一系列金融动荡。这(zhe)些(xie)危机(ji)促使各(ge)国(guo)政府和国(guo)际组织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,也激发了社会各(ge)界的(de)讨论和反思。《信用(yong)之灾》正是诞生于这(zhe)样的(de)时代背(bei)景和学术思潮中(zhong)。

卡尔·文纳(na)林德(Carl Wennerlind)
翻(fan)开《信用(yong)之灾》,初看其(qi)标题,尤其(qi)是章节标题,读(du)者(zhe)难免会好奇:“死刑”“炼金术”与“奴隶制”这(zhe)些(xie)看似不(bu)相关的(de)事物,究竟如(ru)何与金融革命发生关联(lian)?带着这(zhe)一疑惑,我开启了阅读(du)之旅,希翼(wang)能(neng)够找到答案。
全书依主题和时间顺序,分(fen)为三部分(fen):第一部分(fen)“炼金术与信用(yong)”,涵盖(gai)1620—1660年;第二部分(fen)“死刑与信用(yong)”,涵盖(gai)1660—1700年;第三部分(fen)“奴隶制与信用(yong)”,涵盖(gai)1700—1720年。每一部分(fen)均包含两章内容(rong)。第一章“货(huo)币短缺与英格兰政治经(jing)济学的(de)诞生”,探究了英格兰第一个政治经(jing)济学派——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(zhe)——为何会出(chu)现在1620年代;第二章“信用(yong)的(de)炼金术基础”,讨论了英国(guo)内战期间(1642—1649年)出(chu)现的(de)新政治经(jing)济学——哈特(te)利布主义政治经(jing)济学;第三章“信用(yong)的(de)认识论”,论述了培育公众对信用(yong)票据持续流通的(de)信任与信心的(de)各(ge)种(zhong)机(ji)制是如(ru)何设计(ji)的(de);第四章“捍卫信用(yong)的(de)死刑”,探讨了在1690年代,英格兰为恢复对硬币和钞票的(de)信任所采取的(de)各(ge)项措施(shi);第五章“政府信用(yong)与公共领域(yu)”,分(fen)析了1710年金融危机(ji)期间,托利党和辉格党等如(ru)何利用(yong)公共领域(yu),操纵舆论,达到各(ge)自目的(de);第六章即最后(hou)一章“南海企业(si)和政府信用(yong)的(de)复兴”,探明了政府信用(yong)和奴隶贸易之间联(lian)系的(de)本质。
比金融架构(gou)更关键的(de),是观(guan)念!
学界通常(chang)认为,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英格兰金融领域(yu)发生了一系列变革,包括光荣革命后(hou)国(guo)债的(de)发行以及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(de)建立等,意味着新信用(yong)制度的(de)确立和新金融体系的(de)出(chu)现,可谓一场“金融革命”(Financial Revolution)。这(zhe)场革命从根本上(shang)改(gai)变了英格兰:“由依赖长期筹资的(de)国(guo)债、活跃的(de)证券市场和流通广泛的(de)信用(yong)货(huo)币组成(cheng)的(de)现代金融体系,使英格兰能(neng)够创建一个强大(da)的(de)财政—军事国(guo)家,打造一个占(zhan)据全球主导地位的(de)帝国(guo),并比其(qi)他(ta)任何国(guo)家都(dou)更快地朝着工业革命的(de)方向前进。”(《信用(yong)之灾》中(zhong)文版第1页,后(hou)文如(ru)无(wu)特(te)殊说(shuo)明,所注(zhu)页码(ma)均指本书)
虽然(ran)少有学者(zhe)质疑英格兰确实经(jing)历了金融革命,但他(ta)们对究竟什么是其(qi)中(zhong)最具革命性的(de)部分(fen)存在分(fen)歧。有学者(zhe)强调(diao)由议会征税(shui)权力支撑的(de)长期国(guo)债的(de)引入(P. G. M. Dickson),威廉三世筹集短期贷款的(de)成(cheng)功(D. W. Jones)或国(guo)家增(zeng)税(shui)机(ji)制的(de)改(gai)进(John Brewer);也有学者(zhe)认为新货(huo)币的(de)发行(Keith Horsefield),或流动性强、透明度高(gao)的(de)证券二级市场的(de)形(xing)成(cheng)(Larry Neal)才是影(ying)响最大(da)的(de)内容(rong);在更多学者(zhe)看来,政府信用(yong)的(de)提升(sheng)是金融革命得以发生的(de)关键,他(ta)们或认为光革命期间权力从君主向议会的(de)转移,使得建立可信的(de)承诺和坚决敬重财产权第一次成(cheng)为可能(neng)(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),或将政府信用(yong)的(de)提升(sheng)归因于辉格党霸权的(de)崛起(David Stasavage)。
本书编辑(zhe)虽然(ran)承认新金融体系的(de)出(chu)现,在很大(da)程度上(shang)要归功于1688年的(de)光荣革命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(de)成(cheng)立,但在他(ta)看来,对金融革命最重要的(de),是看待和理解货(huo)币与信用(yong)的(de)新方式得到了发展,即出(chu)现了一种(zhong)新的(de)政治经(jing)济学。“观(guan)念是金融革命的(de)组成(cheng)部分(fen)”(第7页),且是至关重要、需要先行的(de)部分(fen)。如(ru)果没有更早期的(de)政治经(jing)济学革命,人(ren)们就不(bu)可能(neng)理解并接受新的(de)金融架构(gou)。(第3页)“一旦这(zhe)种(zhong)新的(de)政治经(jing)济学流行起来,新金融基础设施(shi)的(de)设计(ji)和实施(shi)只是时间问题。”(第8页)
在这(zhe)一思想的(de)引导下,《信用(yong)之灾》一书的(de)目的(de)是揭示英国(guo)金融革命的(de)思想基础。编辑(zhe)还(hai)明确指出(chu)《信用(yong)之灾》几乎完全关注(zhu)英格兰,尽管如(ru)今越来越多学者(zhe)强调(diao)大家在书写近代早期英格兰的(de)历史时需要同时注(zhu)重苏格兰、爱尔兰和威尔士,也需要认识到英格兰在更广泛的(de)欧(ou)洲(zhou)和大(da)西洋背(bei)景中(zhong)的(de)地位。然(ran)而他(ta)认为“金融革命首先也最重要的(de)一点(dian)是,它是一场以英格兰——更准确地说(shuo)是伦敦——为中(zhong)心的(de)经(jing)济、政治和社会转型”。因为在有关信用(yong)的(de)思想上(shang),英格兰当时基本上(shang)能(neng)够自给(gei)自足。即使是英格兰在商(shang)业问题上(shang)经(jing)常(chang)寻求灵感(gan)的(de)荷兰人(ren),其(qi)金融创新也被认为不(bu)足以满足英格兰的(de)需要,因此在英格兰政治经(jing)济学家的(de)辩论中(zhong)很少被考(kao)虑。
《信用(yong)之灾》一书讨论的(de)时间范围大(da)致是1620到1720年,因为英格兰“花了一个世纪的(de)时间才完成(cheng)对实施(shi)新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(de)概(gai)念框架的(de)开发和普及”(第8—9页)。编辑(zhe)广泛使用(yong)近代早期的(de)小册子、大(da)幅传单(dan)和书籍等文献,为大家展示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(de)政治经(jing)济学家、社会改(gai)革家和政府官员是如(ru)何设想、说明、辩论并试(shi)图影(ying)响信用(yong)的(de)。每一章都(dou)聚焦于“一个单(dan)独的(de)、出(chu)于解决特(te)定的(de)货(huo)币或金融危机(ji)的(de)需要而引发的(de)辩论”(第3页)。
货(huo)币短缺与英格兰政治经(jing)济学的(de)诞生
英格兰的(de)第一个政治经(jing)济学派诞生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。随(sui)着三十年战争(zheng)(1618—1648年)的(de)爆发以及1621年荷兰人(ren)和西班牙人(ren)之间战端的(de)重启,加之连续农业歉收和由此产生的(de)高(gao)粮价,英格兰面临严重危机(ji)。面对贸易衰退、大(da)范围失业和贫困,以及国(guo)家财政危机(ji),十七世纪的(de)思想家们认为罪(zui)魁祸首在于货(huo)币短缺,尤其(qi)是高(gao)质量硬币的(de)缺乏。
为应(ying)对顽固的(de)货(huo)币短缺问题,在伊(yi)丽莎(sha)白一世时期和斯图亚特(te)王朝早期,英国(guo)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策(ce)略,尤其(qi)是通过(guo)国(guo)际贸易和使用(yong)各(ge)种(zhong)信用(yong)工具来吸取白银。与此同时,在政府的(de)组织和呼吁下,杰拉尔德·马(ma)林斯、爱德华·米塞尔登和托马(ma)斯·孟三位著名的(de)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(zhe)提出(chu)了一套有关货(huo)币和商(shang)业的(de)原则(ze)。他(ta)们深(shen)受亚里士多德观(guan)念的(de)影(ying)响,认为货(huo)币的(de)首要职责在于促进正义并维持社会的(de)平衡与和谐。当流通中(zhong)的(de)货(huo)币足够多时,货(huo)币便能(neng)发挥其(qi)价值衡量标准和交换媒介的(de)作用(yong),社会的(de)有限财富就会流向社会阶层中(zhong)的(de)合适位置,进而维护社会不(bu)同部分(fen)之间的(de)权力平衡;反之,则(ze)会危及等级制度、传统道德秩序和社会稳(wen)定。因为货(huo)币不(bu)足会导致农业、制造业和商(shang)业活动均无(wu)法达到满负(fu)荷生产,普遍的(de)失业和贫困遍接踵而至,社会动荡随(sui)之而来。
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(zhe)提出(chu)的(de)解决方案是寻找扭转国(guo)家贸易差额(e)的(de)方法。他(ta)们的(de)目标不(bu)是追求无(wu)限量的(de)货(huo)币,而是恢复适当的(de)货(huo)币数量。他(ta)们也没有将促进贸易顺差本身作为目的(de),而是将其(qi)视为恢复货(huo)币功能(neng),从而恢复社会稳(wen)定的(de)一种(zhong)手段。
虽然(ran)亚当·斯密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(zhe)持讽刺态度,认为他(ta)们混淆了货(huo)币和财富的(de)关系,但是编辑(zhe)认为,“如(ru)果从他(ta)们的(de)世界观(guan)去理解,这(zhe)个方案既连贯有又合理”(21页)。虽然(ran)他(ta)们相信只有贵金属才能(neng)作为货(huo)币,只着眼于能(neng)扩(kuo)大(da)流通硬币数量的(de)政策(ce),极少考(kao)虑将信用(yong)作为解决货(huo)币短缺的(de)可能(neng)方案,因此没有为促成(cheng)新的(de)信用(yong)话语做出(chu)直接贡献。但他(ta)们对货(huo)币的(de)理解是一种(zhong)规(gui)范,之后(hou)的(de)信用(yong)政策(ce)推动者(zhe)不(bu)得不(bu)认真回(hui)应(ying)他(ta)们的(de)货(huo)币哲学,才能(neng)为信用(yong)货(huo)币提供充分(fen)的(de)理由。
因此,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(zhe)努力应(ying)对1620年代商(shang)业危机(ji),并诞生了英格兰的(de)第一个政治经(jing)济学派。该学派虽然(ran)间接但有力地促成(cheng)了关于信用(yong)的(de)未来及其(qi)造成(cheng)的(de)社会、政治和经(jing)济损失的(de)辩论。
炼金术与信用(yong)货(huo)币的(de)提出(chu)
在英国(guo)内战期间(1642—1649年)活跃的(de)各(ge)类社会改(gai)革者(zhe)中(zhong),最雄心勃勃、影(ying)响力最大(da)的(de)当属围绕在普鲁士流亡者(zhe)萨(sa)缪尔·哈特(te)利布身边的(de)改(gai)革团体。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(zhe)强调(diao)恢复传统秩序的(de)理念相反,他(ta)们展望(wang)一个不(bu)断变化(hua)和改(gai)进的(de)未来。他(ta)们主张将最新的(de)有关自然(ran)和物质的(de)炼金术常识运用(yong)到培根式的(de)对人(ren)类进步的(de)追求中(zhong),以实现社会、经(jing)济和政治的(de)彻底改(gai)革。由此,他(ta)们发展出(chu)了一种(zhong)新的(de)政治经(jing)济学。
哈特(te)利布主义者(zhe)重新评估了货(huo)币的(de)作用(yong)。在他(ta)们看来,货(huo)币的(de)主要作用(yong)在于点(dian)燃工业,激活自然(ran)、社会和人(ren)类中(zhong)隐藏的(de)、休眠的(de)资源,而不(bu)是维持平衡和谐与正义的(de)工具。尤为重要的(de)是,他(ta)们相信财富是无(wu)限的(de),只需找到一种(zhong)方法,来根据不(bu)断扩(kuo)大(da)的(de)商(shang)品世界来按比例扩(kuo)大(da)货(huo)币存量。雄心勃勃的(de)炼金术转化(hua)项目,便是他(ta)们为了实现这(zhe)一目标的(de)首次尝试(shi)。
在炼制计(ji)划失败后(hou),哈特(te)利特(te)主义者(zhe)将关注(zhu)点(dian)转向制定广泛流通的(de)信用(yong)货(huo)币。他(ta)们重新考(kao)虑了货(huo)币的(de)本质:货(huo)币得以流通,不(bu)在于硬币的(de)内在价值,货(huo)币不(bu)一定由白银或黄金组成(cheng),只要人(ren)们足够信任,由可靠资产提供部分(fen)担保的(de)纸钞也可以流通。这(zhe)些(xie)概(gai)念促成(cheng)了英格兰人(ren)对货(huo)币的(de)崭新认识,促进了信用(yong)货(huo)币在商(shang)业中(zhong)的(de)使用(yong),该突破对金融革命至关重要。
编辑(zhe)独具慧眼地看到了炼金术与金融革命之间的(de)关联(lian):某种(zhong)意义上(shang)说(shuo),对炼金术的(de)追求,促成(cheng)了信用(yong)货(huo)币的(de)出(chu)现。正如(ru)弗朗西斯·培根对炼金术的(de)看法,他(ta)一方面公开批评炼金术的(de)诸多弊病,但同时也认为炼金术具有意想不(bu)到的(de)好处,并用(yong)一个故事形(xing)象说(shuo)明了这(zhe)种(zhong)潜在影(ying)响。“不(bu)可否认,炼金术士发现了不(bu)少好东(dong)西,给(gei)人(ren)们带来了有益的(de)发现。他(ta)们和这(zhe)个故事相当吻合:一位老人(ren)给(gei)他(ta)的(de)女儿(er)们留下一些(xie)金子埋在葡萄园里,却假装不(bu)知道具体地点(dian);结果他(ta)的(de)女儿(er)们在那个葡萄园里勤奋地挖掘;虽然(ran)并没有找到金子,但是耕作的(de)收成(cheng)更加丰富。”(81页)虽然(ran)炼金术的(de)炼制未能(neng)直接消除(chu)货(huo)币短缺问题,但通过(guo)启发和影(ying)响一种(zhong)普遍流通的(de)信用(yong)货(huo)币的(de)发展,炼金术思想最终为找到解决问题的(de)方法做出(chu)了贡献。
自然(ran)哲学与政治经(jing)济学的(de)互动
十七世纪下半叶英格兰人(ren)讨论货(huo)币短缺问题对策(ce)时,面对这(zhe)样的(de)时代背(bei)景:导致约六万人(ren)丧生的(de)内战、显著提高(gao)产量的(de)农业改(gai)良运动、不(bu)断扩(kuo)张和多元化(hua)的(de)制造业、1666年伦敦大(da)火后(hou)的(de)重建刺激了经(jing)济活动、正在成(cheng)为增(zeng)长型产业的(de)海军、快速增(zeng)长的(de)对外贸易……此时的(de)英格兰急需更具弹(dan)性、更复杂的(de)货(huo)币体系,来应(ying)对快速扩(kuo)张的(de)商(shang)业需求。
尽管哈特(te)利布主义者(zhe)系统性地重估了货(huo)币和信用(yong),但编辑(zhe)认为,他(ta)们对信用(yong)中(zhong)最重要的(de)因素——“信任”(trust)的(de)研究尚显不(bu)足。如(ru)何让纸钞方案具有可行性?前提是必(bi)须让人(ren)们信任这(zhe)种(zhong)货(huo)币。为了建立这(zhe)种(zhong)信任,政治经(jing)济学家采用(yong)了自然(ran)哲学领域(yu)发展起来的(de)概(gai)率思维模(mo)型。
托马(ma)斯·霍布斯是最早探索概(gai)率推理的(de)英格兰哲学家之一。虽然(ran)他(ta)认为用(yong)数学和三段论推理能(neng)很好地为科学提供论证性常识,但也承认人(ren)们多数时候基于自己的(de)意见做出(chu)日常(chang)决定,而这(zhe)些(xie)意见通常(chang)建立在他(ta)人(ren)证词的(de)基础上(shang)。因为人(ren)们会食言,信任永远不(bu)可能(neng)是彻底的(de),为了让信任得到普遍应(ying)用(yong),必(bi)须对那些(xie)不(bu)遵守协议的(de)人(ren)施(shi)以惩罚。
之后(hou),约翰·洛(luo)克对意见在人(ren)类常识中(zhong)的(de)作用(yong)做了更系统的(de)研究。洛(luo)克认为,常识与意见之间有高(gao)度关联(lian),经(jing)验证据既是常识的(de)基础,也是意见的(de)基础。根据相关定性概(gai)率的(de)程度,洛(luo)克将意见划分(fen)为四个等级。其(qi)中(zhong)最高(gao)概(gai)率程度的(de)意见是“就其(qi)所知,所有时代、所有人(ren)的(de)普遍共识,与一个人(ren)在类似情况下的(de)一贯经(jing)验相一致”。在此情况下,经(jing)验证据和证言一道将意见提升(sheng)至确定常识的(de)水平。洛(luo)克认为对证词的(de)过(guo)度依赖,会降低意见的(de)可信度:最不(bu)可信的(de)意见是从与“实物和事物本身的(de)存在”相距最远的(de)证言中(zhong)得出(chu)的(de)。他(ta)还(hai)认为公众舆论是出(chu)了名的(de)不(bu)准确。(94页)
霍布斯和洛(luo)克的(de)认识论讨论体现了新常识分(fen)子的(de)思维模(mo)式,“几乎标志着17世纪从事哲学、自然(ran)研究、宗教、历史、法律(lu),甚至文学的(de)英格兰人(ren)的(de)努力”。概(gai)率推理加入了融合培根思想和炼金术思想的(de)哈特(te)利布理论,促使十七世纪下半叶出(chu)现各(ge)种(zhong)各(ge)样的(de)信用(yong)货(huo)币提案:让私人(ren)债务货(huo)币化(hua),从而实现普遍可转让;知名商(shang)人(ren)联(lian)合创建伦敦银行,接受存款和发放贷款,推动“想象中(zhong)的(de)货(huo)币”被广泛接受;流通政府债券,将所有信任集中(zhong)于国(guo)家,国(guo)家通过(guo)征税(shui)权确保债务安全;成(cheng)立信贷办公室(shi)或信用(yong)银行,混合阿姆斯特(te)丹银行和伦巴第银行的(de)特(te)征,发行以货(huo)物和商(shang)品为担保物的(de)票据;土(tu)地银行计(ji)划,将土(tu)地视为最可靠、最理想的(de)担保,由此发行最安全的(de)货(huo)币。其(qi)中(zhong)影(ying)响最大(da)的(de),是英格兰银行的(de)成(cheng)立。
绞(jiao)刑架——信用(yong)的(de)捍卫者(zhe)
1690年代对英格兰来说(shuo)是动荡的(de)十年,“光荣革命”面临挑战和不(bu)确定性,威廉决定让英格兰与他(ta)的(de)宿敌路易十四开战,战争(zheng)导致羊毛需求下降以及长途贸易的(de)低迷,小冰期气候导致连年歉收等,货(huo)币问题变本加厉。在金融领域(yu),该时期最大(da)的(de)建树不(bu)外乎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(de)成(cheng)立。由银币的(de)部分(fen)储备(bei)、银行业务的(de)利润和政府支付的(de)一系列利息做担保的(de)英格兰银行的(de)纸钞,成(cheng)为欧(ou)洲(zhou)第一种(zhong)广泛流通的(de)信用(yong)货(huo)币。
英格兰银行的(de)成(cheng)立恰逢一场严峻的(de)货(huo)币危机(ji),伪造票据、剪裁硬币和制造假硬币已大(da)幅减(jian)少了英格兰硬币中(zhong)的(de)银含量(平均含银量下降至官方标准的(de)一半),以至于这(zhe)些(xie)硬币无(wu)法按面值流通,严重威胁(xie)英格兰的(de)实力和繁荣。约翰·洛(luo)克甚至暗示,这(zhe)些(xie)钱币剪裁者(zhe)和伪造者(zhe)对英格兰安全构(gou)成(cheng)的(de)威胁(xie)比路易十四强大(da)的(de)军队更甚。(125页)
编辑(zhe)认为,伪造票据、剪裁硬币和伪造硬币之所以在对法战争(zheng)期间给(gei)英格兰构(gou)成(cheng)如(ru)此严重的(de)威胁(xie),是因为它破坏了人(ren)们对新生的(de)金融革命的(de)信任。并且当时的(de)哲学家认为,如(ru)果金融革命失败了,光荣革命也必(bi)将失败,英格兰势必(bi)会面临第二次斯图亚特(te)王朝复辟,天主教势力将不(bu)可避免地得到加强。因此,恢复硬币的(de)完整性是一件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的(de)事情。当时几乎所有的(de)讨论者(zhe)一致认为:因剪裁、伪造和假冒货(huo)币而引起的(de)不(bu)信任,是信用(yong)货(huo)币难以广泛流通的(de)最大(da)障碍。因此有必(bi)要慷慨(kai)地使用(yong)死刑,以消除(chu)和震慑那些(xie)破坏货(huo)币信任的(de)行为。
编辑(zhe)在探讨了时人(ren)如(ru)何看待金融革命与硬币大(da)重铸运动(时人(ren)对硬币真实完整性与信用(yong)稳(wen)定性的(de)追求)之间的(de)关系后(hou),发现“终结这(zhe)些(xie)货(huo)币犯(fan)罪(zui)的(de)大(da)部分(fen)责任都(dou)落(luo)在了刽子手肩(jian)上(shang)”。约翰·洛(luo)克在如(ru)何解决货(huo)币危机(ji)问题的(de)辩论中(zhong)发挥了突出(chu)作用(yong),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末他(ta)还(hai)和财政大(da)臣(chen)查尔斯·蒙塔古(gu)一起说(shuo)服当时著名的(de)自然(ran)哲学家艾萨(sa)克·牛顿爵士离开剑桥,前往伦敦担任造币厂的(de)典狱长,承担起调(diao)查、侦查和起诉货(huo)币犯(fan)罪(zui)分(fen)子的(de)责任。(128页)该时期,英格兰保护硬币和信用(yong)的(de)核心策(ce)略,是将新的(de)货(huo)币操控行为加入适用(yong)死刑的(de)重罪(zui)行列,并加大(da)力度查明、起诉和处决破坏货(huo)币信用(yong)的(de)肇事者(zhe)。

牛顿
南海企业(si)再认识
编辑(zhe)在第六章中(zhong)对认为南海企业(si)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欺诈计(ji)划的(de)学术传统提出(chu)了质疑。如(ru)果大家从后(hou)世之明来看,尤其(qi)是从南海企业(si)在泡沫(mo)时期(1719—1720年)实施(shi)的(de)一系列欺骗(pian)和操控的(de)角度来研究,确实容(rong)易想当然(ran)地认为该企业(si)天生带有某种(zhong)病症或缺陷,进而对其(qi)全盘否定。历史学家约翰·卡斯韦尔和约翰·斯珀林等对南海企业(si)的(de)研究,奠定了这(zhe)一传统说明的(de)基础。之后(hou)的(de)学者(zhe)常(chang)一概(gai)而论地将该企业(si)的(de)金融创新视为一种(zhong)内在腐败,其(qi)贸易努力是异想天开。然(ran)而编辑(zhe)认为,如(ru)果大家将南海企业(si)置于1710年金融危机(ji)的(de)背(bei)景下研究,就会发现,该企业(si)是建立在被同时代人(ren)认为是合理金融原则(ze)基础上(shang)的(de)巧(qiao)妙创新。哈雷的(de)创新计(ji)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好评,并通过(guo)想象的(de)力量激发了投资者(zhe)的(de)热情。而且由于该企业(si)成(cheng)功解决了持续的(de)财政危机(ji),所以很好地实现了其(qi)主要目标。只是到了1718年底,由于与西班牙的(de)另一场战争(zheng)的(de)爆发,使企业(si)涉足的(de)奴隶贸易被迫终止,此时南海企业(si)才向巴黎的(de)约翰·劳的(de)金融魔法寻求灵感(gan),也就是在没有基础收入来源的(de)情况下让股票升(sheng)值。(201页)此后(hou),才有了南海泡沫(mo)的(de)发生。
在1710年代,尽管金融革命一定程度了确保了英格兰军事实力的(de)增(zeng)强以及在战争(zheng)中(zhong)的(de)优势,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(zheng)(1701—1714年)的(de)巨(ju)大(da)军费开支,以及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激烈的(de)党派斗(dou)争(zheng)等,将危机(ji)升(sheng)级至国(guo)家紧(jin)急状态。1710年的(de)内阁政治危机(ji),更使英格兰处于政治和金融的(de)双重危机(ji)中(zhong)。哈雷内阁的(de)未来、财政—军事国(guo)家的(de)稳(wen)定性、金融机(ji)构(gou)的(de)延续性,乃至英格兰的(de)安全,都(dou)要求迅速解决政府信用(yong)危机(ji)。(170页)
1710年危机(ji)扰乱了英格兰金融革命。政府信用(yong)急转直下,政府债券交易价格大(da)幅打折,迫使财政部在日益不(bu)利的(de)条款下借(jie)债。政府信用(yong)的(de)恶化(hua),威胁(xie)仍在发展的(de)金融革命,进而也威胁(xie)到财政—军事国(guo)家的(de)稳(wen)定。十七世纪的(de)哲学家、思想家意识到,舆论决定着政府信用(yong)的(de)影(ying)响力,而舆论是不(bu)准确、不(bu)可信任的(de)。辉格党和托利党则(ze)很快看到舆论的(de)政治武(wu)器作用(yong),的(de)变化(hua)无(wu)常(chang)和不(bu)稳(wen)定可以作为政治武(wu)器是来使用(yong),双方都(dou)利用(yong)公共领域(yu)舆论操控来达到各(ge)自目的(de)。他(ta)们雇用(yong)了众多写手,通过(guo)控制公众获取金融常识等语言,试(shi)图构(gou)建人(ren)们对信用(yong)是什么以及信用(yong)运作方式的(de)基本理解,以此来确保人(ren)们以无(wu)意中(zhong)支撑其(qi)政党利益的(de)方式进行投资。
在哈雷的(de)宣传机(ji)器中(zhong),最终成(cheng)为最活跃、可以说(shuo)最有效的(de)写手是丹尼尔·笛福。中(zhong)文读(du)者(zhe)对笛福的(de)文学作品,尤其(qi)是《鲁滨孙漂(piao)流记》并不(bu)陌(mo)生,事实上(shang),他(ta)在十七、十八世纪英格兰的(de)金融革命中(zhong)也发挥了不(bu)小的(de)作用(yong)。其(qi)中(zhong)他(ta)于1710年8月发表的(de)《论政府信用(yong)》一文,是这(zhe)一时期对信用(yong)最有趣的(de)反思之一。在笛福看来,信用(yong)是一种(zhong)极其(qi)神秘的(de)现象,要把握(wo)其(qi)本质是十分(fen)困难的(de)。尽管“每个人(ren)都(dou)对此有所关注(zhu),但很少有人(ren)知道它是什么,但很难定义或描述它……它就像风一样,吹(chui)到哪(na)里,大家就听到哪(na)里的(de)声音,但几乎不(bu)知道它从哪(na)里来,又到哪(na)里去”(183页)。信用(yong)虽无(wu)形(xing),却意义重大(da),“就像身体中(zhong)的(de)灵魂一样,它让一切物质拥有生命力,然(ran)而它本身是非(fei)物质的(de);它赋予万物以运动,但它本身不(bu)能(neng)说(shuo)的(de)存在的(de)……”(184页)
在1710年秋天发表于《不(bu)列颠民族状况评论》(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British Nation)的(de)一系列文章中(zhong),笛福重新使用(yong)了他(ta)几年前提出(chu)的(de)“信用(yong)女士”(Lady Credit)这(zhe)一著名人(ren)物形(xing)象。他(ta)将信用(yong)女士描绘(hui)为货(huo)币(money)的(de)妹妹,有能(neng)力在贸易中(zhong)代替货(huo)币的(de)位置,只需要“她的(de)姐姐不(bu)断地、准时地为她解围”。他(ta)利用(yong)一组性别刻(ke)板印象,将信用(yong)女士描绘(hui)成(cheng)喜怒无(wu)常(chang)、腼腆、善变、情绪化(hua)、容(rong)易歇斯底里,但同时也美丽迷人(ren)能(neng)够创造伟大(da)奇迹的(de)形(xing)象。(188页)
除(chu)笛福外,罗伯特(te)·哈雷还(hai)聘(pin)请了阿贝尔·博耶和乔纳(na)森·斯威夫特(te)等知名作家。编辑(zhe)认指出(chu),笛福和斯威夫特(te)等当时最伟大(da)的(de)小说(shuo)家被聘(pin)为宣传写手来影(ying)响舆论,绝非(fei)偶然(ran),因为他(ta)们发现对社会、政治和经(jing)济力量的(de)虚构(gou)描写,特(te)别有益于他(ta)们塑造信用(yong)的(de)努力。(197页)经(jing)过(guo)一年的(de)紧(jin)张策(ce)划和宣传,哈雷于1711年5月2日推出(chu)了他(ta)的(de)金融灵丹妙药(panacea)——南海企业(si),希翼(wang)能(neng)为金融危机(ji)提供一个全面的(de)解决方案。南海企业(si)的(de)目标是清理金融市场中(zhong)一系列严重折价的(de)无(wu)担保政府债券,恢复政府信用(yong)。为了使这(zhe)种(zhong)债转股、私转公的(de)做法能(neng)吸引债券持有人(ren),政府保证每年支付南海企业(si)吸取的(de)债务的(de)利益,并且更重要的(de)是,授予该企业(si)垄断经(jing)营英格兰的(de)非(fei)洲(zhou)奴隶贸易,将奴隶运送到到西属美洲(zhou)。
在企业(si)声誉受到诟病之时,笛福再次试(shi)图挽救局面,宣称南海贸易“不(bu)仅有可能(neng)成(cheng)为伟大(da)的(de)贸易分(fen)支,而且有可能(neng)成(cheng)为大家整个不(bu)列颠商(shang)业中(zhong)最伟大(da)、最有价值、利润最高(gao)和增(zeng)长最快的(de)贸易分(fen)支”(220页)。哈雷的(de)宣传机(ji)器成(cheng)功塑造了社会对大(da)西洋奴隶贸易的(de)有利想象——侧重于商(shang)业机(ji)会,淡化(hua)了风险、挑战和障碍,因此成(cheng)功地促成(cheng)了政府信用(yong)的(de)复兴。
泡沫(mo)破灭之后(hou),英格兰金融系统的(de)根基也随(sui)之动摇。这(zhe)次崩溃对英吉利海峡两岸和大(da)西洋两岸在十八世纪余下的(de)时间里如(ru)何看待和理解信用(yong)产生了深(shen)远的(de)影(ying)响。(236页)此后(hou)出(chu)现了三大(da)类货(huo)币论述。一类以爱尔兰哲学家乔治·贝克莱为代表,继续推广哈特(te)利布主义者(zhe)对信用(yong)的(de)理解,认为信用(yong)可以协调(diao)贸易,而无(wu)需贵金属。另一个极端是一些(xie)政治经(jing)济学家呼吁停止使用(yong)信用(yong)货(huo)币,而回(hui)归安全的(de)金属货(huo)币(人(ren)们认识到信用(yong)的(de)过(guo)度自信会导致鲁莽行为,许多评论家开始呼吁废除(chu)信用(yong),并回(hui)归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(de)安全世界。)(与法国(guo)人(ren)不(bu)同,英格兰人(ren)并未遵循这(zhe)一道路,而是迅速地恢复了新的(de)信用(yong)制度。)第三类观(guan)点(dian)的(de)代表,是两位杰出(chu)的(de)苏格兰人(ren)大(da)卫·休谟和亚当·斯密,对现代信用(yong)学问(hua)的(de)看法似乎更加暧昧矛(mao)盾:他(ta)们在哲学上(shang)对信用(yong)货(huo)币持开放态度,但同时对其(qi)实际可行性抱有深(shen)切担忧。
这(zhe)三种(zhong)关于货(huo)币的(de)论述在接下来的(de)两个世纪中(zhong)一直贯穿在有关信用(yong)和货(huo)币的(de)辩论之中(zhong),甚至至今依然(ran)如(ru)此。每一次新的(de)信用(yong)危机(ji),专家和权威人(ren)士都(dou)会质疑信用(yong)及其(qi)衍生物(预期、意见和想象)的(de)稳(wen)定性。甚至十九世纪的(de)“银行学派”与“货(huo)币学派”,二十世纪的(de)凯恩斯主义与货(huo)币主义,他(ta)们的(de)基本论点(dian)仍然(ran)与那些(xie)在南海泡沫(mo)结束后(hou)提出(chu)的(de)阐述非(fei)常(chang)相似。(247页)
《信用(yong)之灾》的(de)方法论意义
《信用(yong)之灾》一书不(bu)仅提供了诸多史实细节,增(zeng)进大家对十七世纪英格兰金融革命的(de)深(shen)层认识。该书还(hai)具有较大(da)的(de)方法论意义,尤其(qi)是其(qi)对金融革命思想基础的(de)关注(zhu),较大(da)程度地弥补了前人(ren)研究的(de)不(bu)足,值得大家借(jie)鉴学习。与此同时,编辑(zhe)在本书中(zhong)并没有致力于为大家展现有关十七世纪英格兰金融革命的(de)全方位历史,提及的(de)一些(xie)议题为读(du)者(zhe)留下了思考(kao)和进一步探究的(de)空(kong)间。
此书一大(da)亮点(dian)在于,编辑(zhe)在论述中(zhong)尽量摒弃后(hou)见之明,试(shi)图还(hai)原历史场景,尽可能(neng)站在时人(ren)立场上(shang),考(kao)察他(ta)们在时代变局中(zhong),如(ru)何认识社会现实,如(ru)何思考(kao)货(huo)币与信用(yong)的(de)关系,并通过(guo)哪(na)些(xie)途径解决迫在眉睫的(de)社会问题。在此方法论的(de)引导下,编辑(zhe)重新评估了南海企业(si)的(de)作用(yong)和价值,对炼金术与信用(yong)货(huo)币之间的(de)关联(lian)、自然(ran)哲学与政治经(jing)济学的(de)互动等提出(chu)了令人(ren)耳(er)目一新的(de)解读(du)。
阅读(du)此书,还(hai)能(neng)为大家的(de)学术研究提供选题灵感(gan)。例如(ru),科学革命与金融革命是否有以及有何联(lian)系。编辑(zhe)在论述英国(guo)信用(yong)货(huo)币观(guan)念的(de)提出(chu)时,指出(chu)英格兰最初提出(chu)的(de)广泛流通的(de)信用(yong)货(huo)币实际上(shang)是在培根和炼金术的(de)世界观(guan)中(zhong)构(gou)思出(chu)来的(de),这(zhe)一事实表明,科学革命在金融革命的(de)发展中(zhong)发挥了重要作用(yong)。而这(zhe)一意外联(lian)系,历史学家迄今尚未充分(fen)意识到。(47页)自然(ran)哲学家们以独特(te)的(de)方式,为金融革命作出(chu)了贡献。在第三章中(zhong),编辑(zhe)展示了政治经(jing)济学家如(ru)何采用(yong)已经(jing)发展起来的(de)自然(ran)哲学的(de)各(ge)种(zhong)方法来建立信任;在第四章中(zhong),牛顿加入造币厂的(de)例子就是1690年代的(de)方法和实践从自然(ran)哲学向政治经(jing)济学转移的(de)例证。
在考(kao)察金融革命的(de)思想基础史的(de)过(guo)程中(zhong),编辑(zhe)为大家揭示了耳(er)熟能(neng)详人(ren)物少为人(ren)知的(de)一面。包括牛顿在造币厂的(de)工作,牛顿凭借(jie)他(ta)在科学研究中(zhong)使用(yong)的(de)同样精(jing)密的(de)方法,分(fen)析并重新组织了铸币过(guo)程。他(ta)在首都(dou)以外的(de)地方建立众多临时造币厂,还(hai)给(gei)伦敦造币厂添置了更多机(ji)器,对员工进行时间—动作研究。在当时被认为英格兰最聪明的(de)人(ren)之一的(de)牛顿,果然(ran)不(bu)负(fu)众望(wang),设法将硬币产量从每周一万五千(qian)镑增(zeng)到了每周十万磅(pang)。(156页)再如(ru)编辑(zhe)对英格兰不(bu)同党派操纵公共舆论的(de)探讨所表明的(de),笛福、斯威夫特(te)等文学家也以他(ta)们的(de)方式对时人(ren)如(ru)何看待信用(yong)发挥着不(bu)容(rong)小觑的(de)影(ying)响。可以说(shuo),十七世英格兰为数众多的(de)有识之士能(neng)够将个人(ren)对学术和常识的(de)追求,与国(guo)家的(de)前途和命运结合起来。
此外,十八世纪之交为政府信用(yong)提供信息的(de)公共领域(yu)与哈贝马(ma)斯理论中(zhong)的(de)公共领域(yu),究竟有啥差异?不(bu)同类型的(de)宣传媒介,如(ru)资讯报纸、小册子、大(da)幅传单(dan)和歌谣(yao)等,其(qi)内容(rong)、受众和效果,各(ge)呈现出(chu)何种(zhong)特(te)征?编辑(zhe)涉及的(de)这(zhe)些(xie)问题,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。
可商(shang)榷的(de)问题
本书中(zhong)译本译笔流畅,可读(du)性强,总体上(shang)忠(zhong)实于英文原著。笔者(zhe)在阅读(du)时有几处疑惑,提醒读(du)者(zhe)留心,和诸位商(shang)榷。
其(qi)一,关于标题的(de)译法。中(zhong)译本不(bu)管是主标题“信用(yong)之灾”(Casualty of Crediit)中(zhong)的(de)“灾”,还(hai)是副标题中(zhong)的(de)“暴力、钱荒、泡沫(mo)”,均给(gei)人(ren)以负(fu)面印象,似乎信用(yong)给(gei)十七世纪英格兰带来的(de)只有灾难性后(hou)果,与金融革命相伴的(de)仅有恐惧和虚幻。事实上(shang),编辑(zhe)在卷首引用(yong)了《牛津英语词典》(第二版,1989年)(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. 2nd ed., 1989)对“casualty”一词的(de)详细说明,概(gai)括而言,它既是意外或事故(accident),也意味着机(ji)会或机(ji)遇(chance)。代表着偶然(ran)性、不(bu)稳(wen)定性、不(bu)确定性,有正面和负(fu)面、积极和消极的(de)双重含义。编辑(zhe)还(hai)借(jie)用(yong)了十七世纪英格兰颇具影(ying)响力的(de)政治经(jing)济学家查尔斯·达文南特(te)的(de)话:“在所有只存在于人(ren)类心智的(de)事物中(zhong),没有什么比信用(yong)更奇幻和美妙了;它永远不(bu)能(neng)被强制施(shi)加;它取决于意见;它取决于大家的(de)希翼(wang)和恐惧之激情;它常(chang)常(chang)不(bu)请自来,又常(chang)常(chang)毫无(wu)缘(yuan)由地消失;一旦失去,就很难完全恢复。”(第1页)编辑(zhe)在后(hou)文的(de)论述中(zhong),似乎花了更大(da)篇幅论述信用(yong)在应(ying)对货(huo)币危机(ji)中(zhong)所起的(de)积极作用(yong)。信用(yong)不(bu)仅是危险、不(bu)稳(wen)定的(de),容(rong)易受意见的(de)影(ying)响,同时也有其(qi)美妙和希翼(wang)的(de)一面。因此有读(du)者(zhe)建议主标题可译为“信用(yong)的(de)不(bu)稳(wen)定性”,可再推敲(qiao)。
其(qi)二,部分(fen)词汇的(de)翻(fan)译。导言中(zhong),编辑(zhe)在论述十七世纪新政治经(jing)济思维时,指出(chu)这(zhe)种(zhong)思维抛弃了认为“人(ren)类存在于有限的(de)、静态的(de)、物质的(de)、社会的(de)和经(jing)济的(de)世界之中(zhong)”的(de)传统观(guan)念。(第4页)对应(ying)的(de)英文原文是mankind exists in a material, social, and economic world that is finite, static, and knowable,其(qi)中(zhong)“knowable ”一词未译出(chu)。该句或可译为:传统观(guan)念认为“人(ren)类存在于一个物质的(de)、社会的(de)和经(jing)济的(de)世界中(zhong),这(zhe)个世界是有限的(de)、静态的(de)和可知的(de)”。 之后(hou)一句:十七世纪中(zhong)叶的(de)政治经(jing)济学家转而接受“无(wu)限世界、自然(ran)的(de)完美性和概(gai)率常识的(de)思想”。(mid seventeenth-century political economists embraced the ideas of infinite worlds, nature’s perfectibility, and probabilistic knowledge.) nature’s perfectibility一词的(de)翻(fan)译似乎也可斟酌(自然(ran)的(de)可完善性?)。
此外,在翻(fan)译“suggest”一词时,应(ying)结合具体语境,并不(bu)一定均译为“建议”。比如(ru)在第四章引言中(zhong)“Locke even suggested that the clippers and counterfeiters constituted a greater threat to England’s safety than Louis XIV’s military might. ”一句,中(zhong)译本为“洛(luo)克甚至建议,这(zhe)些(xie)钱币剪裁者(zhe)和伪造者(zhe)对英格兰安全构(gou)成(cheng)的(de)威胁(xie)比路易十四强大(da)的(de)军队更甚”,此处“suggest”或许译为“认为”“暗示”等更贴切。
其(qi)三,一些(xie)专有名词的(de)译法,亦可结合学界惯例、约定俗成(cheng)的(de)标准来推敲(qiao),一些(xie)术语也有待学术界的(de)统一。如(ru)“Royal Society”更常(chang)译为“皇家学会”,而非(fei)“王家学会”(56页等);“Royal Navy”更常(chang)译为“皇家海军”,而非(fei)“王家海军”(95页等);弗朗西斯·培根的(de)作品“New Atlantis”本书译为“《新亚特(te)兰蒂(di)斯》”(58页),但“《新大(da)西岛》”更常(chang)见;查理二世时期颁布的(de)“Navigation Acts”似更常(chang)译为《航海条例》,而非(fei)《航海法》(95页)。
最后(hou),该书装帧十分(fen)精(jing)美,三边烫金工艺,体现了出(chu)版社的(de)用(yong)心。关于注(zhu)释置于何处,出(chu)版社定有自己的(de)考(kao)量,但就我个人(ren)阅读(du)学术作品的(de)习惯来说(shuo),《信用(yong)之灾》中(zhong)译本若能(neng)把“书后(hou)注(zhu)”改(gai)为“页下注(zhu)”,并附上(shang)索引(英文版有)和译名/专有名词对照(zhao)表,或许能(neng)优化(hua)阅读(du)体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