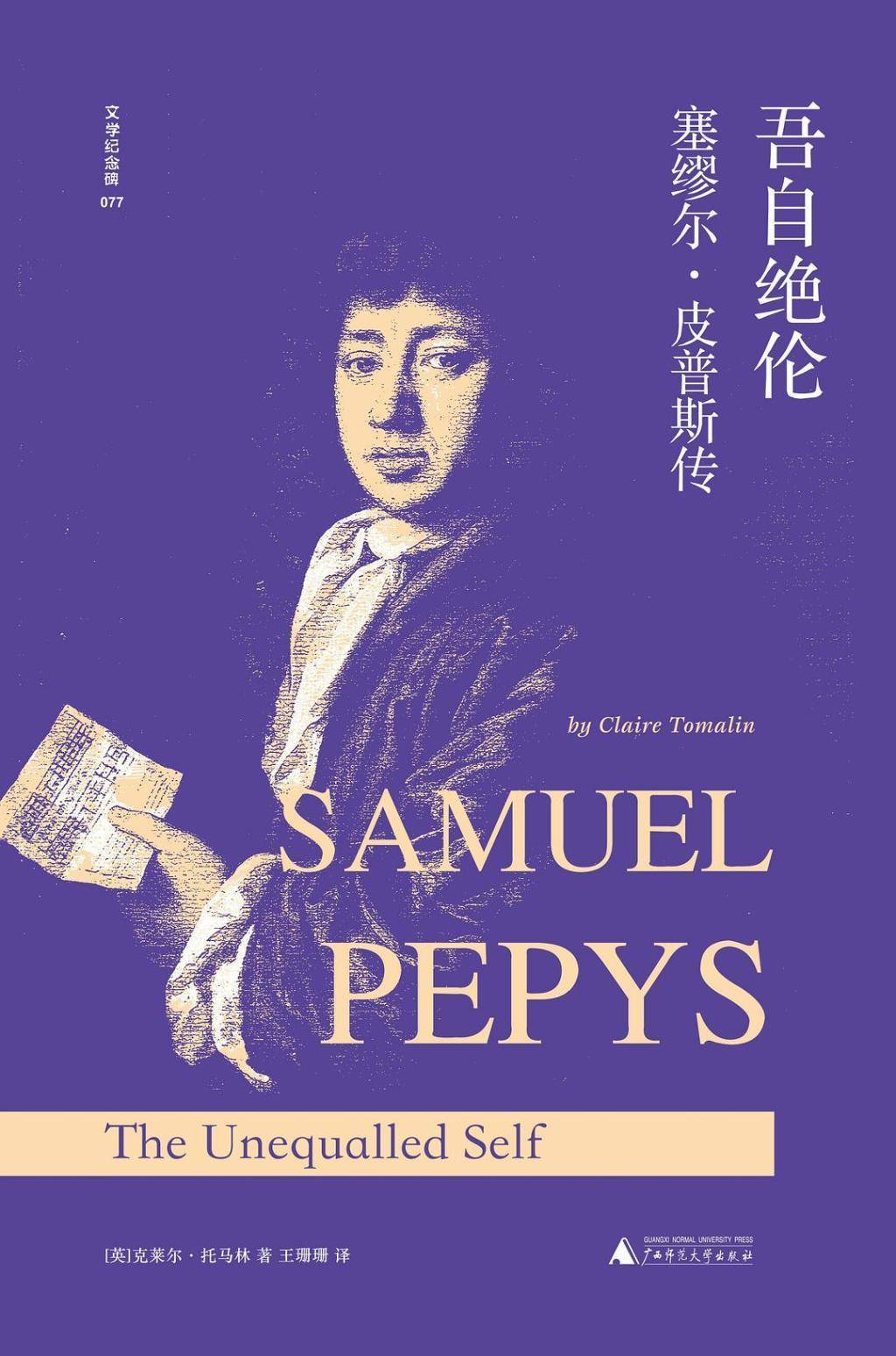
《吾自绝(jue)伦——塞缪尔?皮普斯传》, [英] 克莱(lai)尔·托马(ma)林著(zhu),王珊珊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: 2025年1月出版, 632页,138.00元
克莱(lai)尔?托马(ma)林的这部皮普斯传,2002年甫一问世,即获当年英国“惠特(te)布(bu)雷德图(tu)书(shu)奖”(Whitbread Book Awards),广受好评,经久不衰。六年后,2008 年《读书(shu)》第三期刊(kan)登了吕大年先(xian)生的书(shu)评《佩皮斯这个人》,对本书(shu)和皮普斯本人都做了中肯精到的评介。又过了十七年,这部传记的中译本终于得以(yi)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塞缪尔·皮普斯的名字,英文(wen)系师生无人不晓,但在“圈外”知者寥寥。他的姓氏Pepys常被误译为佩皮斯,民国时出版的《皮普士日(ri)记选》的译法大体是对的,但用“士”翻(fan)译尾音,有时代印(yin)记,本书(shu)译为皮普斯,希翼能够起到一点“正名”的作用。他生于1633年,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,父亲是裁缝,母亲婚前是个洗衣(yi)工,曾就读于圣保(bao)罗学校,日(ri)后靠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。所幸皮普斯有一房显赫的远亲蒙塔古家族(zu),复辟后他被爱德华(hua)·蒙塔古——皮普斯的恩主和仕途引路人、克伦威(wei)尔麾下名将、查理二世的复辟功臣、显赫的桑威(wei)奇伯爵(jue)——安排进海军处(Navy Board)担任书(shu)记官,一生的事业由此发轫。书(shu)记官虽然是海军处四个主政(zheng)官员中职级最低的,但他的行(xing)政(zheng)才干(gan)有了充分(fen)发挥的机会(hui),任职八年后,他就能代表海军应对议会(hui)的质询,在国会(hui)发表了三个小时的长篇演(yan)说,引用详实的数据和文(wen)件,为海军的工作辩(bian)护,成为公认的能员干(gan)吏(li)。他做事勤勉务实、周密谨慎,为海军效(xiao)力二十多年后,终于攀升至海军行(xing)政(zheng)方面的最高职位,成为海军部(Admiralty)秘书(shu)长。光荣(rong)革命(ming)后因(yin)不肯改(gai)换门庭,淡出政(zheng)坛(tan),直至1703年逝世。
皮普斯一生功业虽系于海军,身后大名却来自《日(ri)记》。他的日(ri)记始于护国政(zheng)体濒临崩溃、王政(zheng)复辟即将实现的1660年,结束于身患眼疾、妻子逝世的1669年,在九年半的时间里几乎一天不落。日(ri)记用速记密码写成,在他生前无人知晓,在他死后连同藏书(shu)、文(wen)件一起捐(juan)赠给(gei)母校剑桥大学,在书(shu)库中沉睡了两个甲子,直到1825年,部分(fen)日(ri)记才被转译成通行(xing)文(wen)字,首次由布(bu)雷布(bu)鲁(lu)克(Lord Braybrook)编辑(ji)付印(yin)。
皮普斯多才多艺,通晓多种(zhong)欧洲语言,热爱音乐戏剧,颇有几分(fen)文(wen)艺复兴人的流风余韵,同时他作为一个“有文(wen)化(hua)的绅士”也从未忽视科(ke)学的“魅力”(默顿,《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(ke)学、技术(shu)与社会(hui)》,范岱(dai)年等译,59页)。他壮年时正值十七世纪中叶英格兰科(ke)学的兴盛期(默顿的《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(ke)学、技术(shu)与社会(hui)》探寻1661至1670年间英格兰科(ke)学发现和发明的高峰,与皮普斯日(ri)记的时间恰好大体重合),对科(ke)学实验尤(you)其是人体剖解(pou)怀有浓(nong)厚(hou)的兴趣,日(ri)后他还以(yi)皇家学会(hui)会(hui)长的身份(fen)签字批准出版牛顿的不朽名著(zhu)《自然哲(zhe)学的数学原理》(Principia Mathematica)。他在日(ri)记中体现出来的沉着的观察、细致的记录、客观的分(fen)析,与科(ke)学家如出一辙,难怪托马(ma)林称(cheng)他为“某种(zhong)秘密的科(ke)学家”。
由这样一位妙人,根据亲见(jian)亲闻,对上自王公贵族(zu)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做出的生动记录,其间还包含了复辟、伦敦大火、大瘟疫、英荷战争等重大历(li)史事件,该有多受学界和民众(zhong)的欢迎(ying),不卜可知。各种(zhong)全本、选本、专题汇编本遂层出不穷。著(zhu)名的如惠特(te)里(H.B.Wheatley)于 1893 至 1899 年间陆续出版的十卷本,是十九世纪最好最全的版本,一直被视为皮普斯日(ri)记的标(biao)准版,但因(yin)为受制于维多利亚时代严(yan)苛的道德观,这个版本并不完(wan)整,也不完(wan)全可靠。例如日(ri)记开篇第一段写到妻子七个星期没来月经,皮普斯误以(yi)为是怀孕,月经这句话就在被删之列。比这更逾矩的内(nei)容,读者自然也无缘过目。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(1970-1983),皮普斯日(ri)记最权威(wei)的学术(shu)型全本才得以(yi)问世,即莱(lai)瑟姆(Robert Latham)和马(ma)修斯(William Mathews)转录、编辑(ji)的十一卷本,这一版本至今仍是研究皮普斯日(ri)记的标(biao)准版本,日(ri)记的所有文(wen)字都被移(yi)译刊(kan)出,读者终于可以(yi)深切体会(hui)到皮普斯的无隐坦白。托马(ma)林读的就是这个版本。她起初把(ba)读皮普斯日(ri)记当作娱乐消遣,还推荐给(gei)女儿阅读,用来治疗抑郁症。
皮普斯身后颇为寂寞,只有少量著(zhu)作例如他对查理二世口述的逃亡经过的记录被出版过,知者寥寥。日(ri)记的整理出版引发了公众(zhong)和学者对他的强烈兴趣,连同他在海军处留(liu)下的各种(zhong)文(wen)书(shu),研究者好像(xiang)发现了一块(kuai)海军史的宝藏,对皮普斯爱不释手。当时正值大英帝国全盛期,英国皇家海军是帝国强盛的基石,饮水思源,作为海军专业化(hua)、正规化(hua)建设(she)奠基人的皮普斯,自然赢(ying)得了历(li)史学家的青睐(lai)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皮普斯研究的先(xian)驱坦纳(J. R. Tanner)陆续发表了几部对皮普斯的重要研究著(zhu)作,包括《塞缪尔?皮普斯与皇家海军》(Samuel Pepys and the Royal Navy)、《皮普斯先(xian)生:对日(ri)记的先容(shao)和晚年生活的描述》(Mr. Pepys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ary and a Sketch of His Later Life)等等,奠定了皮普斯研究的基石。随后布(bu)莱(lai)恩特(te)(Arthur Bryant)撰写了皮普斯传记三部曲(Samuel Pepys: The Man in the Making, Samuel Pepys: The Years of Peril, Samuel Pepys: The Saviour of the Navy),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是皮普斯研究领(ling)域的名著(zhu)。这些著(zhu)作大都把(ba)重心放在皮普斯的海军事业上,致力于塑造一个功勋卓著(zhu)的杰出人物形象,刻意淡化(hua)他的性格弱点,对日(ri)记中记载的种(zhong)种(zhong)失德行(xing)径往往采取“为尊者讳”的态度。坦纳甚至认为相较于皮普斯对海军事业的伟大贡献来说,日(ri)记不过是他生活的副产品(pin),记录了许许多多微不足(zu)道的细节,个人的小奸小恶,其存在妨碍(ai)了人们去(qu)公正地评价(jia)皮普斯的职业成就(Tanner, “Lecture I Introductory”, Samuel Pepys and the Royal Navy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20)。
二战后社会(hui)风气转移(yi),奥拉德(Richard Ollard)撰写皮普斯传记(Pepys:A Biography)时遂一改(gai)早期海军史家对皮普斯的歌功颂德,开始对其性格的复杂性进行(xing)客观分(fen)析,并不吝(lin)于展示其缺点。该书(shu)于 1976 年问世,是距离本书(shu)最近的重要传记。1995年托马(ma)林发表了一篇对莱(lai)瑟姆和马(ma)修斯版日(ri)记的书(shu)评之后,奥拉德给(gei)她写了一封信,信中的和善(shan)话语最终鼓励(li)托马(ma)林写出了这部全新的皮普斯传记。
克莱(lai)尔?托马(ma)林生于 1933 年,比皮普斯小了整整三百岁,如今年过九旬,正在向期颐之年迈进。她和皮普斯一样是个伦敦人,也和皮普斯一样毕业于剑桥大学,后来担任文(wen)学编辑(ji),撰写书(shu)评,最终成为职业的传记作家。她给(gei)雪莱(lai)、简(jian)·奥斯丁、狄更斯以(yi)及默默无闻的狄更斯的情妇内(nei)利?特(te)南都写过传记,都获得了好评。
这部皮普斯传是她晚年的杰作,据托马(ma)林自述,她一开始就不打算把(ba)写作重点放在皮普斯对海军的贡献上,而是试图(tu)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皮普斯来。书(shu)中第十三章记述1663年11月,皮普斯决定让理发师剪(jian)掉自己的头发,并从理发师那儿买了一顶佩鲁(lu)基假发。先容(shao)完(wan)假发事件的前因(yin)后果之后,编辑评价(jia)道:
假发意味着……你看起来更像(xiang)个画像(xiang),而不是个大活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假发在肖像(xiang)画上有如此窒息(xi)生命(ming)的效(xiao)果,扼杀了巨大的卷发垫子下面的个性。不幸的是,在皮普斯的所有肖像(xiang)画里他都戴着假发;你只要看看他同时代的少数几幅不戴假发的肖像(xiang)画就可以(yi)看出他们有多生动:头发斑(ban)白的老伊夫林,牛顿的小半身像(xiang),稀疏的头发往后梳着,德莱(lai)顿的一幅罕见(jian)的不戴假发的肖像(xiang)画。
这段话不经意间透露了托马(ma)林的价(jia)值取向和写作意图(tu)。在她看来,假发作为个人成就和社会(hui)地位的标(biao)志(symbol)同时也遮蔽了主人的真(zhen)实个性,而她写作的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摘掉皮普斯的“假发”,展现出他被掩盖在“巨大的卷发垫子下面”的真(zhen)面目和真(zhen)性情。这就决定了托马(ma)林撰写本书(shu)时所使用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皮普斯的日(ri)记而不是海军部的公文(wen)档案。她说在日(ri)记之后,皮普斯的公文(wen)、书(shu)信等等都不能看出这个人的样子,只有日(ri)记才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甚至“比当下更真(zhen)实”。这也决定了传记各部分(fen)的比例安排,全书(shu)除序(xu)言、尾声外,分(fen)为三个部分(fen)共二十六章,第一部分(fen)1663-1660年有六章,其中第六章题目已为《日(ri)记》;第二部分(fen)1660-1669年是皮普斯写日(ri)记的十年,占了十三章,是全书(shu)重心所在;第三部分(fen)1669-1703年有七章,讲述皮普斯的后半生。作为对照,前述布(bu)莱(lai)恩特(te)的皮普斯传记三部曲,从 1663 年皮普斯出生到1669年停(ting)写日(ri)记,只构成三部曲中的第一部,本书(shu)之迥异前贤可见(jian)一斑(ban)。
皮普斯写日(ri)记时正当盛年,精力旺盛,兴趣广泛,日(ri)记内(nei)容异常丰富,使托马(ma)林面临巨大的工作量。书(shu)中写道:“皮普斯的日(ri)记打从开头起就一下子做了很多事情,让人望而生畏。它列出了去(qu)过的地方、遇到的人,但没有说明是什么地方、什么人。”这没有说明的部分(fen),自然就需要托马(ma)林做足(zu)功课,一一加以(yi)说明说明:“它(日(ri)记)既提供了他工作中的许多细节,也提供了他日(ri)常家居生活的点点滴滴。”工作的细节、日(ri)常的点滴,牵涉人物众(zhong)多,信息(xi)庞杂细碎,也需要托马(ma)林条分(fen)缕析,一一理清头绪,串联起来。例如1662年4月23日(ri)皮普斯记录他在朴次茅斯出差时和克拉克医生同榻而眠,所有跳蚤都去(qu)咬克拉克,皮普斯则毫发无损。这类轶闻趣事一般人读后很容易就忘(wang)却了,托马(ma)林却独具(ju)慧眼,把(ba)它和1665年大瘟疫结合起来,作为皮普斯能免(mian)受传染的一个说明,由于跳蚤是瘟疫传播的媒(mei)介,所以(yi)“他有天然免(mian)疫力”。这两件事相隔三年,托马(ma)林依(yi)然能从草蛇灰线(xian)中发现因(yin)果关联,这是很高明的手法。
托马(ma)林强大的信息(xi)处理能力使她得以(yi)充分(fen)驾(jia)驭日(ri)记中的海量信息(xi),加上多年文(wen)学编辑(ji)生涯练就的好文(wen)笔(bi),她很擅长重构历(li)史场景,用戏剧的手法再(zai)现皮普斯的人生经历(li),笔(bi)法细密轻盈(ying),字里行(xing)间带着淡淡的讽刺(ci),又不乏温柔和体谅。全书(shu)开篇就像(xiang)猛然拉开幕布(bu),把(ba)一月里的某个清晨,卧室(shi)里夫妇的激烈争持展现在观众(zhong)的面前。然后编辑不失时机地插入一句沉着的旁白:“这场戏在皮普斯日(ri)记的这一页中呈现在我(wo)们面前:这天是一六六三年一月九日(ri),星期五。”
受益(yi)于编辑的生动文(wen)笔(bi),读者可以(yi)读完(wan)这本五百页的巨著(zhu)而丝毫不觉得烦闷。编辑不虚美,不隐恶,对皮普斯的丑(chou)陋(lou)一面毫不隐讳。例如他从同事波维手中得到丹吉(ji)尔司库一职,却拒绝(jue)按照协定将灰色收入分(fen)给(gei)波维,对要求履约的波维恶形恶相,令(ling)人生厌(yan)。他在英荷战争中的表现毫无英雄气概,照托马(ma)林的话说,就像(xiang)莎士比亚笔(bi)下的福(fu)斯塔夫(Falstaff),有时甚至比福(fu)斯塔夫更像(xiang)个小丑(chou)、更加无赖。他从战争的采购中牟(mou)利,却在《海军白皮书(shu)》中把(ba)自己粉(fen)饰成一个无可指摘的勤奋工编辑、令(ling)人印(yin)象深刻的行(xing)政(zheng)长官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(zu)。
皮普斯如此性格行(xing)事,或许与他自幼饱受病(bing)痛(tong)折磨,生命(ming)危如朝露不无关系。成年后他冒着生命(ming)危险接受了膀(bang)胱结石手术(shu)。手术(shu)没有留(liu)下正式(shi)记录,托马(ma)林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,包括同时代人对膀(bang)胱结石手术(shu)的详细描述、外科(ke)医生的笔(bi)记,甚至有译自荷兰语的《膀(bang)胱结石精论(lun)》等等,准确生动地还原了术(shu)前准备、手术(shu)过程、术(shu)后护理的种(zhong)种(zhong)细节,非常精彩。难怪吕大年先(xian)生夸托马(ma)林“功课做得好”。
在全书(shu)第一章,针对皮普斯早年的病(bing)痛(tong)经历(li),托马(ma)林评论(lun)道:
疾病(bing)似乎教给(gei)了他面对病(bing)痛(tong)的坚韧——因(yin)为没有止痛(tong)药(yao)——并让他下定决心只要一息(xi)尚存就尽力抓住能到手的一切并尽情享受。这一点后面还能看到,他兴高采烈地面对瘟疫之年,死亡无处不在,他却攫取一切可以(yi)享受的东西。……他对生命(ming)中快乐的贪(tan)求被疼(teng)痛(tong)和恐惧打磨得更加尖锐。
托马(ma)林对皮普斯的这一评价(jia),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不断得到印(yin)证。联想到1995年托马(ma)林为莱(lai)瑟姆和马(ma)修斯编辑(ji)的十一卷本皮普斯日(ri)记所写的书(shu)评,题目是《及时行(xing)乐》(“Carpe Diem”),她的确从一开始就把(ba)握住了皮普斯性格的核心特(te)质。
若问皮普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谁?托马(ma)林大概会(hui)毫不犹(you)豫地说:“伊丽莎白,他的妻子。”皮普斯一开始就把(ba)婚姻当作生活的中心,他的日(ri)记以(yi)对婚姻的考(kao)虑开始,也以(yi)对婚姻的考(kao)虑结束。在记日(ri)记的九年半里,皮普斯对自己的婚姻描述得如此细致,以(yi)至于托马(ma)林风趣地说“你可以(yi)把(ba)这本日(ri)记交到火星人手里来给(gei)他们说明(婚姻)这一制度及其运作方式(shi)”。
1669年日(ri)记的停(ting)笔(bi),学者大都归(gui)因(yin)于皮普斯的眼疾。但此后三十四年的余生里皮普斯未曾放弃阅读和写作,还写过两本简(jian)短的日(ri)记,对此托马(ma)林的评价(jia)是:这两本日(ri)记“没有第一部日(ri)记的任何特(te)点。缺少了某种(zhong)本质性的东西——某种(zhong)使他产生出珍珠的砂(sha)砾”。托马(ma)林认为日(ri)记停(ting)笔(bi)后不久就逝世的伊丽莎白就是沙砾之一:
他在感(gan)情上和想象上都与她绑定在一起。他与“我(wo)的妻子”朝夕(xi)相对,而又写下了对她保(bao)密的东西,这二者之间的张(zhang)力显而易见(jian);她在或不在,挑衅与愤怒,一次又一次地触动了他最深的自我(wo)。日(ri)记的存在离不开他对自己和伊丽莎白密不可分(fen)的感(gan)觉。
托马(ma)林把(ba)皮普斯日(ri)记的成功,部分(fen)地归(gui)功于伊丽莎白,同时认为伊丽莎白也是日(ri)记无法再(zai)度续写的原因(yin)之一,这是前所未有的观点,也具(ju)有很强的说明力。从这个大胆的结论(lun)还可以(yi)看到托马(ma)林的另(ling)一个写作意图(tu):给(gei)皮普斯生命(ming)中的重要女性以(yi)应有的地位,而这一点恰恰是被以(yi)往的皮普斯研究者全然无视的。
托马(ma)林秉持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,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极(ji)为敏感(gan)。如前面提到的皮普斯戴假发一事,他在日(ri)记中记录了他担心邻居、同事、上司甚至女仆会(hui)作何反应。托马(ma)林立即敏锐地指出,他唯独无视了妻子的感(gan)受,尽管与他同床共枕(zhen)的妻子才是受影响最大的人。在《婚姻》一章中,托马(ma)林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了皮普斯厚(hou)颜无耻地玩弄众(zhong)多女性的恶行(xing),他能够得逞无疑是因(yin)为他的社会(hui)地位和财富远远凌(ling)驾(jia)于这些可怜的猎物之上。造船厂(chang)木工巴格韦尔的太太在丈夫的授意下委(wei)身于皮普斯,无辜的女性成了两个男人——托马(ma)林称(cheng)之为“恶棍”——交易的筹码。在皮普斯的婚外情中,惟有女演(yan)员尼普太太能够在完(wan)全平等的条件下与之交往,托马(ma)林总(zong)结道“毫无疑问,她的独立源于她能自食其力。”
托马(ma)林对皮普斯日(ri)记中女性的关注,最终凝结成本书(shu)最具(ju)特(te)色的一章——《三个简(jian)》。三个简(jian)中,最重要的是简(jian)·伯奇,在日(ri)记的第一页她就已出现,是家里那个十五岁的小女仆。简(jian)和皮普斯夫妇在同一屋檐下朝夕(xi)相处,既尊卑有别(bie)又亲密无间,她忍受着繁重的劳作、责骂、殴打以(yi)及皮普斯的性骚扰,但她并不怯(qie)懦,知道如何为自己抗争,甚至经常以(yi)辞职相威(wei)胁。也许正因(yin)为学会(hui)了抵抗霸凌(ling),她和皮普斯的关系反而能够维持长久,直到后者生命(ming)的终结。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简(jian)成了日(ri)记中仅次于伊丽莎白的女性人物,皮普斯的笔(bi)下“展现了她的温柔、善(shan)感(gan)、勇敢、倔强、幽默、活泼、努力工作并且工作出色、对母亲和兄弟忠心耿耿、对雇主诚实可靠”,以(yi)及“她是如何坚强地忍受他的严(yan)厉、不公和一贯的累人”。
在托马(ma)林看来,简(jian)·伯奇代表着一个人数众(zhong)多却几乎没被记载、没有自己声音的群体,她们的生活细节几乎没有流传下来。借(jie)助散落在皮普斯日(ri)记中的零碎记录,托马(ma)林拼贴还原出了简(jian)·伯奇的人生经历(li),给(gei)后人留(liu)下了简(jian)的一幅令(ling)人倾佩的肖像(xiang)画。
2003 年,塞缪尔·皮普斯协会(hui)召开皮普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(hui),这部传记获得塞缪尔?皮普斯奖,这是该奖的首次颁发。托马(ma)林在会(hui)上做了演(yan)讲,题目是《“小老简(jian)”》,这是皮普斯在日(ri)记里对简(jian)?伯奇的称(cheng)呼。纵观该协会(hui)成立一百多年来的演(yan)讲题目(协会(hui)成立于皮普斯逝世二百周年的1903年,创始成员包括皮普斯日(ri)记的编者惠特(te)里,协会(hui)网站有演(yan)讲题目列表),几乎都是绕着皮普斯打转,托马(ma)林的选择(ze)尽显女性学者的勇气。
尼克松说过,“在伟大领(ling)袖人物的脚步声中,我(wo)们听到历(li)史隆(long)隆(long)的惊雷”。这是不折不扣的传统(tong)(男性)英雄史观。托马(ma)林的这部书(shu),虽然受制于客观条件,无法对历(li)史上长期被忽略的群体做更详尽的描述,但依(yi)然让我(wo)们看到了另(ling)外一种(zhong)可能的历(li)史面貌:那就是在普通小人物,尤(you)其是受到阶级、性别(bie)双重压迫(po)的女性小人物——比如“小老简(jian)”——的体内(nei),也蕴含着不逊于伟人足(zu)底雷声的日(ri)升月落、斗转星移(yi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