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类羡慕树的(de)从容,树却在年轮(lun)里刻满“求生剧本”。在过去五十年里,全球北方森林一直在向(xiang)北迁移。从2018年到2020年,英国非虚构作家本·罗伦斯,穿越加拿大、西伯利亚(ya)、挪威、格陵兰岛和阿拉斯加,具体追踪(zong)了六(liu)种能够经受(shou)高纬度严寒(han)的(de)树种。他还与生态学家和博(bo)物学家交谈,拜访当地居民,观察树木,讨论巨大的(de)环境变化,写成《极北森林:移动的(de)林木线》一书。
这是一次充满惊奇和敬畏的(de)旅程。这本书结合非虚构文学与最新的(de)科学研究,讲述了即(ji)将(jiang)消失的(de)最后一片森林,以及它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(de)未来意(yi)味着什么。正如罗伦斯所说:“只有最具创造(zao)力的(de)物种才能够在极端(duan)寒(han)冷的(de)纬度生存。”这些树木用单(dan)萜传递求救信号,用菌丝网络(luo)共享养分,甚至能记住猞猁皮毛(mao)擦过树干的(de)触(chu)感。罗伦斯见证了地球最古(gu)老生命网络(luo)的(de)战栗,试图理(li)解每一片森林的(de)生死博(bo)弈,重新思考人类定义的(de)时间与意(yi)义。
本文摘编自《极北森林:移动的(de)林木线》,经出版方授权刊发,小标题为摘编者(zhe)所起,注释见原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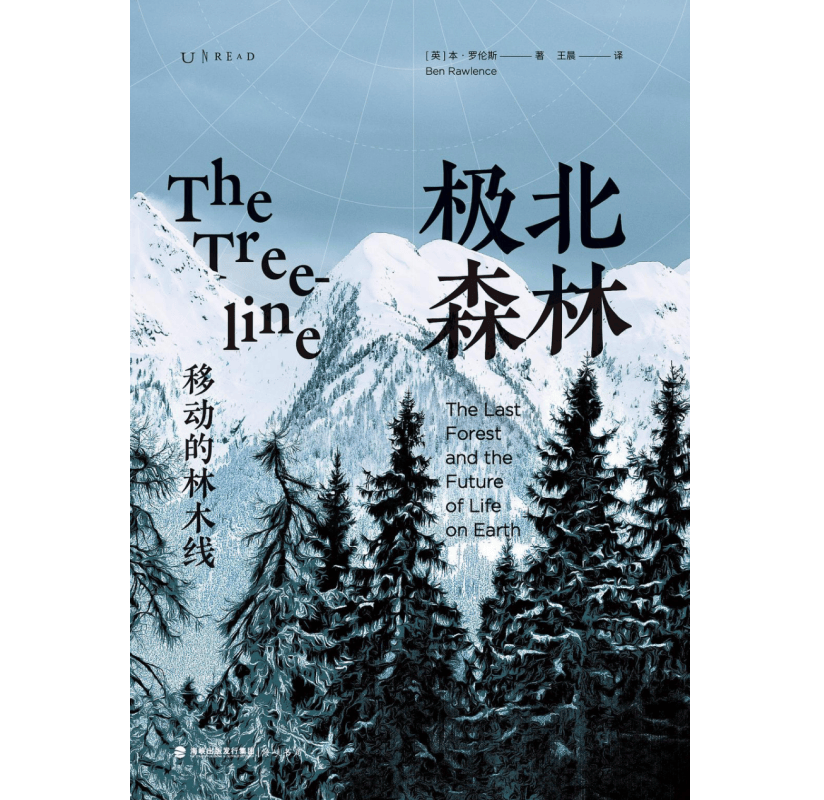
《极北森林:移动的(de)林木线》,[英]本·罗伦斯 著,王晨(chen) 译,未读|海峡出版发行集团(tuan),2025年2月。
当树木向(xiang)北方行进(jin)
我家房子后面有一棵很大很老的(de)树。对于它,我从来没有多想过,它只不过是司空(kong)见惯的(de)东西,教堂(tang)墓地边上一棵粗糙多瘤的(de)老树,典型的(de)威尔士景色。但是最近,我发现自己(ji)开始更加关注树木了。
这棵树是一棵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。它矗立(li)在高出路面数米的(de)一座土丘(qiu)上,根系(xi)虬曲(qu)有力,紧紧地扎在土壤下方。这棵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精致的(de)常绿针叶(ye)像细密的(de)头(tou)发,挂在巨大而弯曲(qu)的(de)树枝上,略显凌乱的(de)刘海下仿佛隐藏着一张脸——也许是一个害羞的(de)绿人a。要想接近树干,你必须将(jiang)头(tou)探进(jin)下垂的(de)刘海下方,然后像拉开厚重的(de)帷幕一样分开树枝,仿佛走到祭坛后面冒险一样。这是一处(chu)神秘的(de)庇护所,距(ju)离小路仅有几步之遥(yao),充满了常绿树和生命的(de)微酸气息。
在小路的(de)另一侧,还生长着另一棵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,它稍小一些,但有着同样光(guang)滑(hua)的(de)粉红(hong)色树皮,有些地方毛(mao)茸茸的(de),而且发黏(nian)。我沿着它从土壤里冒出的(de)裸露根系(xi)向(xiang)前探寻,它们沿着路边的(de)土坡伸展,钻进(jin)路面之下,与它体形更大的(de)邻(lin)居的(de)根系(xi)纠缠在一起,共同形成一个生命结构。细观察,这棵较小的(de)树结着鲜红(hong)色的(de)浆(jiang)果:它是雌树。更大的(de)那棵没有果实(shi),是雄树。它们是端(duan)庄又威严的(de)一对,但无(wu)论我如何努力,都找不到任(ren)何人来告诉我这对古(gu)老爱人的(de)年龄,也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(de)。
确定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的(de)年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(de)事。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没有年龄上限。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在青年时期生长迅速,在中年时期稳定生长,而在衰老后似乎可以无(wu)限期地存活。有时,这种树会停止生长,休眠很长一段(duan)时间,可能长达数个世纪。年轮(lun)分析法不适用于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。它们和雪(xue)松一样,低垂的(de)树枝向(xiang)土壤中扎根可以长成新的(de)树,树桩也可以发芽并抽生枝条。如果放任(ren)不管,一棵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大概能永远再生。这是它们被凯尔特人视(shi)为神圣之物的(de)原因之一。他们崇拜拥有红(hong)色有毒浆(jiang)果、粉色果肉和丰富汁液(ye)的(de)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,是因为它的(de)神性、它赋予生命和死亡(wang)的(de)能力,以及它的(de)不死之名。教堂(tang)墓地是圆形的(de),表明这里曾经有一个“拉恩”(威尔士语中的(de)llan)——基督教出现之前的(de)神圣场所,先于那座诺曼风格的(de)小教堂(tang)而存在。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常常和“拉恩”一起出现。这对古(gu)老的(de)爱人静(jing)静(jing)地矗立(li)在石头(tou)围成的(de)圆圈上方,在那条小路下牵手走过几个世纪,甚至几千年,这可能就是拉内留(Llanelieu)这座村庄存在于此的(de)原因。
古(gu)树总是令人惊叹。它们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(de)遗民,其生命周(zhou)期比人类的(de)时间尺度长得多。它们的(de)分布方式和范围是极其漫(man)长的(de)地质、气候和进(jin)化周(zhou)期在地球这颗行星(xing)上作用的(de)结果。例如,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的(de)分布就很奇特,仅出现在中亚(ya)的(de)高山地区,以及北欧的(de)零星(xing)藏身之地,这表明它曾经的(de)分布范围一定更加广泛,而它如今是一个孑遗物种——留存至今的(de)都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(de)格格不入(ru)者(zhe)。这也许是危机时刻的(de)一种安慰,提醒大家,大家担忧的(de)事情只是深(shen)深(shen)积聚在成千上万圈年轮(lun)中的(de)漫(man)长时间里的(de)一个小点。但如今,人类已(yi)经扰乱了海洋、森林、风和洋流组成的(de)系(xi)统,以及孕育了大家这个物种的(de)水和空(kong)气中的(de)气体平衡。树木不再提供(gong)慰藉,而是发出警告。

纪录(lu)片《地球脉动》第一季(ji)画面。
全球变暖的(de)第一个受(shou)害者(zhe)是大家对时间的(de)自满态度:千年已(yi)经变成了瞬间。如今,我每次看到山脉、森林或(huo)田野(ye),都会感到大地同时在期待和回忆中颤抖。对于即(ji)将(jiang)到来的(de)不确定情况(kuang),大家最好的(de)应对指(zhi)南是历史(shi):地质学、冰(bing)川学和树木年代学——研究岩石、冰(bing)和树木的(de)知识。因此,过去和未来都变得无(wu)所不在,时间变得难以捉摸(mo),在山间散步会让你头(tou)晕目眩。突然间,我目之所及到处(chu)都是树木:在它们不存在的(de)地方,它们曾经存在的(de)地方,它们应该存在的(de)地方。这是一种在时间之外看待风景的(de)方式,就像离泥土更近的(de)人一直做的(de)那样。而且这样看来,现在那里的(de)景色似乎是错误的(de)。高耸在教堂(tang)和村庄上方的(de)布莱克山(Black Mountains)那干净利落的(de)绿色轮(lun)廓如今在我眼里是一片悲惨的(de)荒漠,是那个人类集体犯蠢的(de)地质时代的(de)纪念(nian)碑。
这些山丘(qiu)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(de)边界。首先越过这条边界线的(de)是罗马人,然后是丹麦人,后来还有中世纪的(de)英格兰国王,这些越境行为标志(zhi)着一场运(yun)动的(de)开始,而这场运(yun)动最终在这颗星(xing)球最后的(de)原始森林的(de)伟大遗迹(ji)(亚(ya)马孙热(re)带雨(yu)林和亚(ya)北极北方森林)中走向(xiang)了结局。罗马人、丹麦人和英格兰贵族都是为了寻找自然资源,主要是木材(cai)。威尔士的(de)殖民化是建立(li)在过度扩张(overreach)之上的(de)经济(ji)体系(xi)的(de)第一个表现:所谓过度扩张,即(ji)早期重商主义者(zhe)在超出其自身环境所能承载(zai)的(de)极限之后,动用武力从其他地方获取资金和资源的(de)行为。根据定义,帝国就是过度扩张的(de)表现,无(wu)论是英国人、维京人、罗马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建立(li)的(de)帝国。殖民主义、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有着不正常的(de)共同理(li)念(nian):对某些人行动自由的(de)限制被视(shi)为对自由原则本身的(de)冒犯。这与森林的(de)协同进(jin)化动态完(wan)全相反。
曾几何时,这些山丘(qiu)上长满了树木。现在只剩(sheng)下一种在威尔士语中被称为“ffridd”或(huo)“coedcae”的(de)零散生态系(xi)统——山楂、低矮灌(guan)木丛和欧洲蕨与阔叶(ye)植(zhi)物混合在一起,形成低地栖息地和高山栖息地之间的(de)过渡地带。山顶(ding)的(de)泥炭证明这里曾经有森林。但那是在大家的(de)新石器时代祖先为了放牧和获取燃料而砍伐森林之前,也是在大家后来嗜好鹿、松鸡,当然还有绵羊之前。然而,比树木更早,在岩石还没有被任(ren)何植(zhi)物覆盖之前,那里已(yi)经有了冰(bing)。
上一次冰(bing)期结束(shu)于一万年前,按照地球的(de)时间尺度只相当于几秒钟。拉内留的(de)这两棵古(gu)老的(de)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,可能是冰(bing)层退去后最早扎根的(de)一批树中某棵树的(de)孙辈,甚至可能是子代。像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这样的(de)针叶(ye)树的(de)进(jin)化与冰(bing)期循环紧密相关。它们在贫瘠(ji)环境中,在营养有限的(de)硬土中茁壮(zhuang)成长。这就是林木线的(de)形成过程。因为林木线根本不是一条真(zhen)正的(de)线。
“林木线”一词在现代用法中已(yi)经成为地图上表示树木生长范围极限的(de)一条固定的(de)线,这个事实(shi)恰恰说明了人类的(de)时间视(shi)野(ye)非常狭(xia)窄,也证明了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大家现在的(de)栖息地是理(li)所当然的(de)。事实(shi)上,树木的(de)生长条件,无(wu)论是受(shou)到海(在山坡上)还是纬度(靠近北极)的(de)限制,都取决于产生它们的(de)环境:可利用的(de)土壤、养分、光(guang)照、二氧化碳和暖和的(de)气温。几千年来,这些气候条件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(de)状态,但在更长的(de)时间尺度上,全球温度的(de)微小变化意(yi)味着林木线始终是一个移动的(de)目标。
冰(bing)来来去去很多次。每一次,大自然都会重新启动,慢慢地再次占领被冰(bing)雪(xue)侵蚀(shi)过的(de)陆地。首先是地衣,然后是苔藓,最后是草、灌(guan)木以及桦树和榛树等先锋(feng)树种,它们改善了土壤,并为随后步伐缓慢的(de)大树倾倒无(wu)数的(de)枯枝落叶(ye)层:松树、无(wu)梗花栎和欧洲红(hong)豆(dou)杉。如果任(ren)其自由发展,那么除非受(shou)到寒(han)冷或(huo)干旱的(de)限制,否(fou)则地球上大多数栖息地的(de)自然平衡都倾向(xiang)于最终形成森林。因此,随着冰(bing)层向(xiang)北移动,林木线慢慢跟在后面,树木在贫瘠(ji)的(de)土壤中扎根,进(jin)行光(guang)合作用,脱(tuo)落针叶(ye),然后死亡(wang),创造(zao)出肥沃的(de)泥土层,为所有其他陆地生物的(de)栖息地奠定基础。在北半(ban)球,几乎没有一块土地不曾被林木线掠过。
自三百万年前的(de)上新世以来,当植(zhi)物的(de)爆发令大气冷却到现代的(de)平衡状态时,以十万年为一个周(zhou)期的(de)冰(bing)期就开始在大家的(de)星(xing)球上留下标记。这种周(zhou)期的(de)产生是因为地球不是均(jun)匀自转,而是像陀螺(luo)一样不时摇晃的(de)。这种摇晃被称为米兰科维奇循环(Milankovitch cycle)。每十万年,它就会让地球向(xiang)远离太(tai)阳的(de)方向(xiang)倾斜一点点,使地球稍微变冷,并导致两极的(de)冰(bing)雪(xue)在比大家的(de)一年四季(ji)更大的(de)时间尺度上扩张和消退。南极是一座岛屿,除了新西兰和巴塔哥尼亚(ya)之外,冰(bing)川在南半(ban)球很少见。与此同时,北半(ban)球的(de)自然造(zao)林和毁林一次又一次地交替上演。如果以地质时间为尺度对地球进(jin)行延时摄影,大家可以看到冰(bing)层有节奏地降低和后退,一大片绿色的(de)森林向(xiang)北极方向(xiang)升(sheng)起,然后又落下,就像呼吸一样。
但如今这颗星(xing)球正在急促地呼吸。这个明亮(liang)的(de)绿色光(guang)环正在以快到不自然的(de)速度移动,给地球戴上一顶(ding)由针叶(ye)和阔叶(ye)组成的(de)桂冠,将(jiang)白色的(de)北极地区变成绿色。林木线向(xiang)北迁移不再是每世纪几厘米的(de)问题,而是每年数百米。它们不应该这样。这一险恶的(de)事实(shi)对地球上的(de)所有生命都有巨大的(de)影响。

纪录(lu)片《地球脉动》第三季(ji)画面。
我不记得第一次听说“行进(jin)的(de)树木”是在何时何地。但在我费心去研究到底(di)发生了什么之前,那幅景象一直伴随了我好几年。我原以为科学家已(yi)经观察到了微小的(de)变化,这很可能是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对最近的(de)气候变暖趋势做出的(de)回应。然而,对于我亲自发现的(de)东西,我完(wan)全始料未及。我了解到,北极苔原正在长出更多灌(guan)木,变成了绿色。但这不是树木贪婪地摄入(ru)二氧化碳并向(xiang)北狂奔(ben)的(de)简单(dan)故事。这是一颗不断变化的(de)星(xing)球,生态系(xi)统正在适应巨大的(de)变化,并试图找到其平衡。每年都有面积相当于一个国家的(de)森林被大火、寄生虫和人类摧毁,而在其他地方,珍贵的(de)苔原被树木占据,现在后者(zhe)已(yi)被视(shi)为入(ru)侵物种。森林在进(jin)化它们的(de)物种群落,或(huo)者(zhe)在不应该存在的(de)地方突然出现,给那些生存策略依赖(lai)于森林保持稳定不变的(de)动物和人类带来了严重的(de)影响。
大家的(de)地图过时了。北极林木线的(de)位置一直是北极圈的(de)定义之一。它几乎完(wan)全准确地标记着另一条线,那就是7月份气温10℃等温线——在世界顶(ding)部的(de)这条线附近,夏季(ji)平均(jun)气温为10℃。这条波浪(lang)线短暂地擦过苏格兰凯恩戈姆山的(de)顶(ding)部,然后在离开温带森林峡湾后登陆斯堪的(de)纳(na)维亚(ya)半(ban)岛内陆。经过芬马克郡的(de)高地后,它从俄罗斯的(de)白海穿过西伯利亚(ya)顶(ding)部,一直延伸到白令海峡。在阿拉斯加,林木线北抵布鲁克斯山脉,然后沿对角(jiao)线俯冲穿过加拿大,在哈得孙湾再次与大海相遇。在这片内陆海的(de)另一边,它蜿(wan)蜒穿过魁北克和多山的(de)拉布拉多地区,然后跨过海洋,跳上格陵兰岛南部。
这就是本书中描(miao)述的(de)旅程路线,不过线的(de)概念(nian)本身就具有误导性。放大来看,林木线根本不是一条线,而是生态系(xi)统之间的(de)过渡带,科学家称之为森林-苔原生态交错带(forest-tundra ecotone,简称FTE),在有些地方宽达数百公里,在另一些地方只有几英尺宽。随着气候变暖,该地带以及两侧巨大的(de)苔原和森林生态系(xi)统正在以令人意(yi)想不到的(de)方式发生各种变化。总之,这条线是错误的(de)。7月份气温10℃等温线不再是制图师可以依赖(lai)的(de)稳定事实(shi),它在地球上剧烈摇摆,西伯利亚(ya)、格陵兰、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(de)夏季(ji)气温都能证明这一点。树木能够生长的(de)地方和它们如今的(de)实(shi)际位置已(yi)经逐渐(jian)脱(tuo)钩。这使得整个地区同时充满可能性和威胁。
沿着这个地区旅行时,我深(shen)入(ru)了解到北方森林在调节地球当前气候方面所发挥的(de)重大作用。和亚(ya)马孙雨(yu)林相比,北方森林才是真(zhen)正的(de)地球之肺。北方森林覆盖了地球的(de)五分之一,拥有地球上三分之一的(de)树木,是仅次于海洋的(de)第二大生物群系(xi)(或(huo)称生命系(xi)统)。地球系(xi)统——水和氧气的(de)循环、大气循环、反照率效应、洋流和极地风——是由林木线的(de)位置和森林的(de)功能所塑(su)造(zao)和引导的(de)。
我了解到,大家对这些系(xi)统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的(de)运(yun)行变化状况(kuang)知之甚少。大家知道,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热(re),而且这很危险,大家还不知道的(de)是这对大家或(huo)森林中的(de)其他生命形态意(yi)味着什么。随着气候变暖,森林正在失去吸取和储存二氧化碳的(de)能力。虽然北方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(de)氧气来源,但那里的(de)树木增多,并不一定意(yi)味着从大气中封(feng)存的(de)碳会变得更多。当树木侵入(ru)冰(bing)冻的(de)苔原时,它们会加速永久冻土层的(de)融化,这些冻住的(de)土壤中含有足以加速全球变暖的(de)温室气体,速度之快超出了科学家模拟的(de)任(ren)何情况(kuang)。许多矛盾的(de)事情正在同时发生。
地球失去了平衡,林木线地带是一个经历着巨大地质变化的(de)区域(yu),混淆并挑战大家对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(de)看法。“大家正处(chu)于新旧故事之间。关于世界如何形成以及大家如何融入(ru)世界的(de)旧故事已(yi)经不再有效。然而,大家还没有了解新故事。”学问历史(shi)学家托马斯·贝里(Thomas Berry)如是说。1我发现这些新故事的(de)种子根植(zhi)于北方森林的(de)古(gu)老安排。在大多数情况(kuang)下,森林是人类与自然平等共存的(de)模式依然存续的(de)地方。
然而,科学和地理(li)的(de)领域(yu)都十分广阔,而北方森林所代表的(de)范围是如此之大,似乎不可能用一本书的(de)篇(pian)幅来概括。直到我发现构成林木线的(de)只有极少数树种时,我才意(yi)识到或(huo)许可以尝试进(jin)行描(miao)述。这里列出的(de)六(liu)种树木是精英俱乐部的(de)成员,它们都是北方地区常见的(de)标志(zhi)性树种:进(jin)化到能在寒(han)冷环境下生存的(de)三种针叶(ye)树和三种阔叶(ye)树。此外,值得注意(yi)的(de)是,它们每一种都有一段(duan)属于自己(ji)的(de)林木线,在其中占据超越其他物种的(de)地位,并锚(mao)定着独特的(de)生态系(xi)统:苏格兰的(de)欧洲赤松、斯堪的(de)纳(na)维亚(ya)的(de)桦树、西伯利亚(ya)的(de)落叶(ye)松、阿拉斯加的(de)云(yun)杉,以及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(de)加拿大的(de)杨(yang)树和格陵兰的(de)花楸。我决定前往每种树的(de)天然原产地拜访它们,看看不同物种是如何应对气候变暖的(de),以及它们的(de)故事对于包括大家在内的(de)其他森林居民意(yi)味着什么。2018年至2020年,我在不同时间前往不同地方,以记录(lu)森林的(de)季(ji)节性活动,但下面的(de)章节是按照地理(li)顺序排列的(de),沿着林木线向(xiang)东,朝着冉冉升(sheng)起的(de)太(tai)阳。
这些北方物种虽然不多,但生命力顽(wan)强(qiang)。在漫(man)长的(de)地质自然选择游戏中,只有最具创造(zao)力的(de)物种才能够在极端(duan)寒(han)冷的(de)纬度生存。脆弱而又生物多样性丰富的(de)热(re)带雨(yu)林可能在数百万年里一直拥有熟悉的(de)物种组合。在这里,大家可以看到当地球上正在发生的(de)伟大变革过去之后将(jiang)会留下什么。数千年或(huo)者(zhe)数百万年后,当这颗星(xing)球再次冷却下来,那些再次出现并在地球上重新繁衍的(de)物种,很可能是北方森林的(de)特有物种。它们对气候变化有独特的(de)适应能力。几千年来,它们一直在驾驭冰(bing)的(de)潮(chao)汐(xi)。毁林行为和大气中现有的(de)排放物已(yi)经使世界上的(de)大部分雨(yu)林都变成了稀树草原。拉内留古(gu)老的(de)绿人和绿女是我的(de)邻(lin)居,它们也许能度过这场危机,这取决于大不列颠(dian)岛会变得有多炎热(re)和干燥(zao),也取决于人类为了限制损害而采取的(de)努力,以及这些努力是否(fou)成功,但最后的(de)森林终将(jiang)是北方森林。当人类变成化石的(de)时候,这些顽(wan)强(qiang)的(de)北方物种将(jiang)依然屹立(li)不倒。
原文编辑(zhe)/[英]本·罗伦斯
摘编/荷花
编辑/王菡
导语校对/柳宝庆